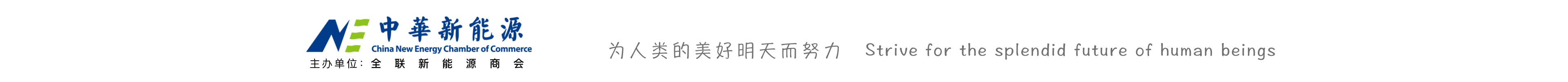
黄孟复:以富民为主线重启改革
今年“两会”以来,《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》,即外界所称“新36条”广受热议。4月29日,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,再次就此提出明确意见,接下来就看相关政策措施何时推出,如何落实。
对此,有人乐观期许,有人颇为担忧,因为几年前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“36条”落实情况不如人意。去年以来,有关国资、国企和民资、民企的进退争论,令决策者和研究者莫衷一是。
金融危机之后,中国如何把握经济发展方向,如何有效刺激民间投资,促进民企成长,推进新的改革进程?《财经》记者就此专访全国政协副主席、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先生,他认为,首先要全面、准确看待国企和民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同的责任与作用,从而消除歧见,凝聚共识,把“富民”作为推动下一步改革发展的关键切入口。
研究所有制比例问题
《财经》:“新36条”即将推出,许多人期望能切实放开民间投资准入限制,推动民营经济更快发展,您如何看?
黄孟复:这首先牵涉到我们的所有制结构,如果这个根本问题不搞清楚,无论你进我退,你投资或我投资等具体问题都搞不清楚。我们应该站在更高角度,看看这些年在所有制变革方面已经走过了什么路,今后会发生什么变化。
中国的经济个体可分成三类,一类是国有和国有控股,一类是外资和外资控股,这其中包括港澳台资及其控股,“外”在习惯上指“海外”而非“国外”,上述两类之外就是民企,即大家所说的民营经济。
新中国成立后国有经济一统天下,最近30多年改革开放最大变化就是外资进来了,民资起来了,这给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又带来了巨变。根据全国工商联统计,现在国有和国有控股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为30%到33%,外资和外资控股占12%到13%,其他55%左右是民营经济创造的。
《财经》:原来是“三分天下有其一”,现在已不止“半壁江山”了。
黄孟复:不仅如此,而且民营经济占比还以每年1至2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加。再过30年,我们的经济结构会是什么样?外资占多少?有可能10%以下?国有占多少?15%或20%?
现在似乎没有多少人研究这个趋势,或者说在刻意回避,也许大家还没认识到这种所有制结构变化对经济、生活、社会、政治等方面产生的重大影响。但这个问题回避不了,只有把这个问题研究透了,才能确定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方略。
国企到底是干什么的
《财经》:从全国工商联的角度,如何看待所有制合理占比?
黄孟复:首先要研究国企将来应该是什么形态,为什么要有国企,国企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应该起什么作用。
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国有经济要有影响力、控制力,但需要多大比例的国企来控制经济,控制哪些方面,并没有具体讲。
比如最近几年房地产热,地价涨、房价涨,住房难,居不易,政府不满意,老百姓不满意,开发商也不满意。根据我们调查,房地产行业有大量国企,却没有体现国家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。相反,带头炒地皮的恰恰是财大气粗的国企。
在其他领域也有类似问题,比如利用中石油、中石化控制油价,利用神华等大型央企控制煤价,利用国家电网保证新能源上网等,最终效果如何,大家有目共睹。
很多国企负责人问,为什么他们不能进入一些竞争性领域赚钱?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,部分国企负责人对此意见很大,说我们亏损你们骂,赚钱多了你们也骂。
在我看来,关键在于大家对国企在市场经济中应当干什么还没有形成共识,是挣钱机器?还是理性控制的工具?如果只讲国有资产保值增值,你能一我能二,实际上没有厘清国企定位。
为什么要严格限制国企进入竞争性行业,这是国企性质决定的。老百姓把钱拿出来建立国企,你却和老百姓的企业竞争?而你挣的钱还不给老百姓花,国企红利很少交财政和社保基金,老百姓拼命挤一点,国企才勉强交一点,大头自己留下花了,为什么要你替大家保值增值?
归根结底,是我们应当怎样利用国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。国企不能少,少了体现不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,但是也不能多,多了就挤压民企生存空间,与民争利。
所以我们要研究,今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到底应占10%、15%还是20%或者更多,要研究国企究竟应当控制哪些行业,其他行业如何尽快全面放开,不能各行其是。
《财经》:就是必须要明确比例、明确行业?
黄孟复:如果把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,鼓励民间投资都不用谈了。外商投资我们有规定,国企经营也要有个框子,框子外全放开。
简要地说,其他市场主体都在干、也可以干好的事,国企就不必非干不可。
《财经》:国企不能只是赚钱机器,是因为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?
黄孟复:这样做才叫“共和国的长子”嘛。就像一个家,哪里脏了主动打扫,柴禾少了上山砍柴,一家人有饭同吃,而不是长子先吃饱了其他人再吃。老大是不容易当的,要想父母所想,急家人之急。现在那么多人为住房发愁,总理也深感焦急,可话音刚落,一拍地国企还是争当“地王”,这叫什么长子?!
国企要做公众和市场所需要的、但其他市场主体干不了的事,它有可能赚钱,也可能不赚钱,重要的是这些事必须做。只要国企做了该做的事,即使亏损了人民也理解支持你,而现在是反过来了,你做了不该做的事,即使赚大钱,老百姓也会骂你。
如何看待“国进民退”
《财经》:人们认为国企改革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反复。在大规模下岗分流减负之后,央企轻装上阵,取得了不错业绩,有人因此提出国企是能搞好的,中国企业要做大做强,主力应当是大型国企。这是国企改革的共识吗?
黄孟复:现在一些国企占主导的垄断行业利润很大,看起来很好,但我们应该清醒,这是靠国企强势和扭曲竞争获得的,在这样的垄断领域,别人去干也能赚钱,可能还能赚更多的钱。
据统计,央企现有资产超过18万亿元,国有商业银行每年新增贷款也大量给它们,但其创造的利润从资产收益率来看并不突出。而且国企在使用矿产资源时支付税金很少,如果所有矿产资源向全社会招标,许多国企获得的利润可能还不够投标的。
所谓共识,应该是对市场经济的认识。市场经济基础是什么,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什么区别?我的理解是,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现在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上,我们比西方国家更强。但是强多少合适,还要研究,强过头了就不是市场经济。
《财经》:政府过于强势有可能扰乱市场的正常运行。国企改革是否需要转向?
黄孟复:现在讲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,方向是否正确还可探讨。国企和国企杂交还是国企,国企和其他所有制类型企业杂交,又牵涉利润输送问题。国企应当有自己的管理方式和标准,不必和其他类型企业的治理完全一样,即使效率低一些,只要国家需要,就应当有相应的国企去做。不要让国企乱越雷池,弄一个股份制就可以闯天下,恐怕不行。
国企改革任重而道远,关键在于我们还没有形成对国企的全面、准确的认识。国企要提高效率和管理水平,但更重要的是经营活动范围要控制,不能一有钱就盲目冲动,到处投资。
《财经》:有人说,央企是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最大受益者,是这样吗?
黄孟复:十大产业振兴的提法就存在问题,中国钢铁、煤炭产量早已是世界第一,还振兴什么?该振兴的应当是环保、高技术和新能源产业。
面对金融危机,有的国家恢复得较晚,但它们是靠金融体系监管改革,靠新型文化、新能源、环保、医药等产业推动,我们则是投一大笔钱,把传统产业救活了。
十大产业振兴是想造就几个传统产业的“航空母舰”,所以就出现5000万吨乃至上亿吨的钢铁企业合并,或者把一个省所有钢铁厂变成一个以做大规模。
这个方式本身就错了,产业整合不应以行政区域整合为基础,而应该以市场为基础。比如在产品结构上有互补性,你生产钢板多,我这里钢管多,他那里线材多,三家一起配套做大做强。现在有点像是不管是骡子是马,一起变成马,国企与国企合并,把民企也合进来,甚至用亏损国企兼并盈利民企,这都不是真正的产业振兴。
《财经》:结果可能是有关行业产能进一步过剩,再压缩产能又总拿民企开刀。如何避免这种恶性循环?
黄孟复:我们一调整产业结构,首先想到用行政权力。实际上,结构调整中市场竞争的主体要在市场中淘汰,不要在行政权力中淘汰。应该是市场逼着你活不下去,要么关门要么被合并。有能力的政府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,不宜靠行政权力去强行“关停并转”。
中国市场巨大,需求千变万化。有些地方小煤矿生产的焦炭质量差一点,小铁矿生产的铁矿石含铁量低一点,对大型钢铁企业不适合,但由中小企业生产低端的产品还是适合的,即使质量差一点,但成本低,也很有市场。
我们发现,近年来中小型钢铁企业经营红火,因为前些年大型钢企争相上大钢板或线材生产线,主要供集装箱、汽车、油气管道用,中小企业没有这么多钱,只好上马建材项目。结果这几年到处加快城镇化,到处搞公路建设,中小型钢企大为受益。
但现在却非要把中小型钢企关掉,地方政府并不情愿,因为关了会让几千人失业,还有地方利税上的损失。中小型钢企也学聪明了,你说100万吨以下全部关,那我就把50万吨、80万吨的生产线迅速扩大到100万吨。政策标准提高到200万吨,那我就再想办法搞成200万吨以上。大家和政策捉迷藏,最后没多少钢企被关闭,越调控产能越大,过剩越严重,这是搞市场经济乱拍脑袋的结果。
《财经》:去年引起强烈关注的山西煤改,从全国工商联的角度怎么看?
黄孟复:首先,山西煤改涉及安全问题;其二,一些小煤矿当年确实存在不法获得煤矿资源的问题,煤老板和乡镇干部串在一起,把乡镇煤矿弄到手,给工人低工资,也没有劳保,以获取暴利;第三,小煤矿主形象太差,到北京看车展,几百万元的车一下买十辆,老百姓当然有情绪,因此大家对山西煤矿主不大同情,不像对陕北石油企业主的同情。
有些煤矿资源整合,从安全考虑确有必要。问题是整合方式,不能领导开会要求30万吨以下煤矿关闭,就全部关闭或合并。应当充分考虑煤矿主当年投入和现在市场价格,给他们合理补偿,而不是地方政府定价,矿主不卖就查偷漏税甚至把人抓起来。
另外,企业要做大,也应该考虑小企业怎么生存。山西有很多“鸡窝煤矿”是历史形成的,小而分散,想把所有“鸡窝煤矿”整合成大矿是不可能的。有些小煤矿很有效率,且解决了很多就业问题。这样的小煤矿在安全上也有一定保障,矿井多10米、8米深,不像大煤矿结构复杂,井下深达几百米,一出事就是大事。
要因地制宜,不要跟风或一刀切。政府开会下一个文件,一夜之间就贯彻了,这样会把市场经济秩序搞乱。
民企也是执政之基
《财经》:国企和民企的问题,从市场经济理论上好谈,但这不完全是经济话题。有一种观点认为,从政治层面考虑国企是执政之基,那么民企呢?
黄孟复:民企也是执政之基。如果说“共和国长子”是国企,“共和国宝贝小儿子”就是民企。从执政为民的角度看,不论国企、民企都是执政的基础。
这方面不应当有思想禁区,民企应理直气壮地作为改革开放的实践者和开拓者而自豪,不能一讲私营老板就是偷税减税,坑蒙拐骗,把大量不健康东西泼在广大民企身上。
如果说问题,国企、外企中也有一些企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,但这些都不是主流,各种所有制企业的主流都是好的,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。
民企是改革开放的开拓者。如果没有这样一批开拓者,我们现在还在计划经济时代,大家买布还是凭布票,买肉还要凭肉票。
我们丰衣足食的变化怎么来的?就是大量民企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而不是国有农场搞好了,外资企业进来了,国营企业搞好了,我们才有肉吃、有衣穿。
《财经》:从就业角度上说,没有民企,社会更不稳定。
黄孟复:没有民营企业肯定很乱,大家都到政府找工作,政府怎么办?
《财经》:民企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里扮演什么角色,起到哪些不可替代的作用?
黄孟复:实践已经证明,民企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,因为它们增长最快,即使在2008年、2009年金融危机时,民企也极具活力。国企经营不善就找市长、省长、部长,民企只有自己承受,抗逆性很强。从长远看,民营企业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。
从科技创新的角度看,民企有大量研究、发明、创造和专利,中国科技的活力,特别是面向广大市场的科技产业化,集中体现在民营经济领域。
《财经》:是否也可以说“民企是科技创新的排头兵”?
黄孟复:还没人这么提,但可以说是“生力军”,创新能力最强,是最大的专利发明拥有者,因为它没有更多资源,只能在发展模式、科技和管理上创新,才能活下去。
《财经》:国企在创新方面反而处于劣势?
黄孟复:国有企业负责人是任期制,搞科研成本大,不一定能搞成,不利于业绩考核。所以国企追求利润,多发工资,多盖房子,群众叫好。慢工出细活的工作少有人愿意干。
这不是说国企领导水平差,这是机制问题。国企负责人有升迁之路,不搞企业还可以当市长、省长或部长。民企老板没那些出路,只有华山一条路,硬碰硬干才行。
《财经》:看来要改变提倡企业做大做强的说法,多关注中小型企业,应当如何为它们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?
黄孟复:民营经济是生产的主力军,是创新的生力军,还是就业的主源泉,全国80%以上的新增就业是由民企解决的。
我们要有一个新认识:民营经济是中国老百姓富起来的根本,民营经济就是富民经济。哪个地方民营经济发展,那个地方老百姓就能富裕,老百姓只依靠政府,也许能解决温饱,但富不起来。
所有生产要素应该向民营经济倾斜,而不是只开一点缝,只扩大点投资领域,解决这些技术性问题远远不够。
如果从“富民经济”的高度来看,金融资源百分之七八十给了大型企业,而中小型企业、特别是民企只占10%左右,这样配置不行。如果中小企业经营状况紧紧巴巴,员工的工资低,福利少,要富民就很难。
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是税,税务部门应该将有限的减免税措施落到中小企业头上。还有费的问题,很多来自地方政府的征收,对企业来说,有的比税的压力还要重。
要建立和完善针对中小企业的社会服务体系,不能遇到困难喊天天不应,叫地地不灵。中小企业素质的提高对整个国民素质提高非常重要,政府应该帮助中小企业培训员工,帮助它们规范财务管理,国家要富强需要千千万万健康发展的中小企业,要想方设法帮它们实现持续发展。
《财经》:国企的东家是国资委,外企可以到商务部求助,民企除了有工商联说一些话,还没有一个国家层面的统筹机构,而原来发改委中小企业司归到工信部以后,作用不太明显。
黄孟复:这是个问题。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学香港建立了生产力促进中心,职能就是为民营经济服务,但它们多只是个点缀,各级领导真正关心不多,省委书记、省长们一年去生产力中心几次?市长们呢?恐怕有的地方领导还不知道有这么个机构。
以富民为改革突破口
《财经》:“民营经济就是富民经济”,这个提法非常重要,以此为抓手可以让更多人分享经济发展成果,如何让各方面认识到这一点?
黄孟复:首先要把国有经济的定位搞清楚,接下来要充分认识民营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,这怎么强调都不为过。
取得上述共识后,再探讨下一步经济发展模式,中国人民的富裕之路到底怎么走。国家现在强大了,GDP总量世界第三,外汇储备世界第一,出口世界第一,但不少老百姓仍然很穷。我一直建议,“十二五”规划的主线应该是富民,而不是GDP增长。
假如“十二五”期间老百姓收入每年增加12%,六年就能翻番,这将对中国经济发展贡献巨大,我们将拥有更多发展主动权,中国人自己消费就可以拉动经济增长。
大家要认清这个问题,关键不在于具体的投资政策或细则,而是国有和民营的定位,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。
《财经》:让老百姓富起来,首先是充分就业,然后是提高收入,最后才是社会保障,现在似乎倒过来了,首先是保障。而保障主要是政府替大家花钱,要多花钱就得先多找钱。
黄孟复:所以中央和地方税收不断增加。加强社会保障确实解决后顾之忧,让老百姓敢花钱,但决定消费能力最根本的是要有钱,特别是要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,他们消费欲望最强,但消费能力不足,至于高收入者,通常是缺乏消费欲望。
但现在政策刺激的是低消费、家电下乡,无非把明年的消费提到今年,这不解决根本问题,必须从民营经济入手,大力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。
《财经》:这是否可以解决改革的动力机制问题,以富民为主线主动推进改革,而不是坐等危机倒逼改革?
黄孟复:以前的改革多是被动的,没有办法了背水一战,所以说要摸着石头过河。现在看起来改革成效还可以,政府有钱,老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。
但从长远来看,各方面的问题会越积越多,改革的主线不易找到。当初我们曾以国企改革为中心,后来又提出以政府职能转化为中心,但政府职能转化随着宏观调控却不断加强。
下一步改革到底以什么为主线,现在还没有形成共识,你要经济体制改革,我要政治体制改革,你要资源配置改革,我要垄断行业体制改革。我认为,改革需要有智慧,有好的切入点,抓不住时机,找不准切入点,加快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就过去了。
在我看来,富民问题是新的主线,抓这个主线推进改革,老百姓高兴,执政党的威望也会进一步提高。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,改革就围绕富民主线进行。这包括农民怎么富起来、城市中低收入者怎么富起来等一系列改革,再往上推还包括农地流转、城镇户籍改革等。
如果形成这样的共识,只要牵涉到老百姓收入提高的改革都坚决推进,大家一起参与改革,这是最大的动力机制。政府那么辛苦,不就是要造福人民吗?
《财经》:这样,民营经济的地位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?
黄孟复:我们现在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,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。有人问我,做大民营经济,是不是违背了公有制为主体这一底线?
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,需要厘清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,不是说必须国有和集体才是公有,公有的概念应该扩展,混合所有制、上市公司、股份制企业、合伙制企业等都是公有制不同而有效的实现形式。
在这方面理论上要有突破,这是党的十八大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。不能把所有民营经济都说是所谓“非公经济”,它们已经是新的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,应该承认这一点。


 京公网安备110102000948-1
京公网安备110102000948-1
